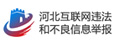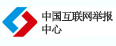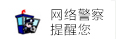发布时间:2020-04-20 点击量:6401
2020年4月9日,新华社受权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该项意见首次将“数据”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传统要素并列为要素之一,并提出要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若要促使数据要素获得市场化与规范化的应用,首先就必须清晰厘定数据资源在私法意义上的权利属性。在现行域内外法律制度框架下,数据垄断行为之所以很难得到全面、周延、有效的规制,主要原因就是数据的权利属性依旧处于模糊不清状态。迄今为止,世界各国立法者尚未能够清晰厘定数据产生者、控制者、使用者、分析者各自对数据资源具有何种权益。譬如,在德国法律制度框架下,只有少数类型的由经营者深度加工的数据资源可被认定为经营者的精神财产权客体,而其他类型的数据资源的权属并不清晰。
在互联网相关市场领域,由于垄断企业的自我持续强化导致市场集中度日益提升,因而由少数几家寡头垄断平台企业占据大量由社会公众产生的数据资源成为常态化存在。少数几家寡头垄断平台企业甚至可能最终控制整个社会商务资源。这些海量数据资源不仅具有极大的经济价值,而且直接涉及社会公共安全利益、国家安全利益与消费者隐私利益。基于维护公共利益、国家利益与个人权利视角,我国立法机关有必要修订现行反垄断法、网络安全法、民法以及其他法律,清晰厘定这类由社会公众产生的数据资源的非私有属性,并授权特定监管部门实施常态化的数据要素市场监管行为,以确保数据资源的收集、管理、分配、利用都符合公共利益的要求。
进一步而言,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据服务将成为社会公众日常不可或缺的生活服务类型之一。基于此,我国立法机关可以借鉴欧盟关于普遍经济利益服务(services of general economic interest)的法定保障模式,将与社会公众基本生存相关联的基本数据服务纳入公共产品范畴,确保任何人不能私自控制这类基本数据服务的供给,而应当由所有社会个体以经济上可承受的代价自由地与平等地获取这类基本数据服务。如果经济弱势群体成员无法以经济上可承受的代价自由地与平等地获得这种基本服务,作为公共利益代表的国家就应当主动实施介入措施,介入分为以下两种途径:其一,由国家设立国有企业直接生产并免费提供相应基本数据服务;其二,通过国家监管与国家补贴方式,委托特定企业生产这些服务并以成本价提供给社会公众。
2016年,斯洛文尼亚制宪机关具有开创性地在《斯洛文尼亚宪法》中规定,水资源不是商品,而是由国家管理的公共资源,并且公民获得饮用水的权利是宪法基本权利。基于此宪法规定,水资源不能被商业化生产、运营与分配。我国立法机关可以考虑借鉴斯洛文尼亚制宪机关的立法思路,将社会公众所产生的大数据资源厘定为非商品化的由国家监督与管理的公共资源。这类大数据资源的商业化利用不得损害公共利益,也就是说,它们只能基于公共利益视角被生产、分配与利用。
在全世界范围内,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是迄今最为严苛的关于个人数据保护的法律文件。它所规制的数据领域不法行为范畴不仅涵盖数据垄断行为,而且亦涉及侵犯消费者权益行为。总体而言,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是一个理想型的数据规制法律模板,但是该条例相关数据保护理念与义务设定过于超前,因而它并不符合我国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现状。举例而言,欧盟实施《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之后,诸多中国企业、美国企业就停止了在欧盟内部市场的经营活动,其原因在于,这些企业在欧盟的数据合规成本远远大于盈利。因此,对于我国而言近期立法机关或执法机关有必要从数据垄断规制角度制定相关数据保护条例或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但是这类法律文件中关于数据保护义务与责任的设定标准不宜过高,尤其应当避免由于法律过度规制而扼杀处于初始发展阶段的数字经济的后果。
必须引起关注的是,在数字经济时代世界各国的利益同中存异,相互之间具有竞争关系与利益冲突。譬如,欧盟正寻求在制定国际数据流动与保护规则层面掌握主导权,并进而构建欧盟主导的全球数字单一市场。欧盟已经在《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框架下与美国、日本、瑞士、加拿大等国订立“数据流动”适当性决议;依据这一协议约定,欧盟成员国和欧洲经济区(EEA)成员国以及美国、日本、瑞士、加拿大等国形成国际数据自由流动区域。“数据流动”适当性决议的签订无疑有助于参与协议国家的企业降低数据合规成本。然而,在国际数据流动与保护规则制定层面,以我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与以欧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具有迥然不同的利益诉求。为了防范我国在将来成为数据跨境流动领域的“国际孤岛”,我国政府一方面应当主动参与国际数据流动与保护规则的协商、交流、制定与修订进程,争夺国际规则制定话语权,尽快创设中国版本的国际数据流动与保护规则;另一方面应当依托既有本土跨境数据流动规制制度,通过与其他国家或国家联盟对等订立“数据自由流动”双边或多边协议的方式,建构与拓展以我国为主要参与方的世界性数据自由流动区域,避免受到欧美国家的挤压、孤立与隔离。
基于数字经济的微观视角,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实施的不正当限制竞争行为日益引起社会关注,它们可能竞合违反《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电子商务法》等法律。举例而言,在腾讯封禁飞书事件中,从《反垄断法》第17条分析,腾讯公司涉嫌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垄断行为。具言之,从传统市场份额界定角度分析,腾讯企业在企业协作办公相关市场应被推定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从互联网经济规模效应、锁定效应考虑,腾讯公司在企业协作办公相关市场上亦应当被推定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腾讯公司利用这种市场支配地位,排挤竞争对手,对相对方施加压力,这就涉嫌构成《反垄断法》禁止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垄断行为。此外,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2条第2款第(三)项,经营者不得利用网络技术手段,通过影响用户选择或者其他方式,恶意对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实施不兼容。在腾讯封禁事件当中,腾讯公司涉嫌利用技术手段,全面封禁竞争对手飞书公司合法提供的远程办公产品,所以构成变相形式的不兼容行为。此外,腾讯公司的封禁行为还涉嫌构成违反《电子商务法》第35条的限制交易行为。不过,从有效维护合法权益角度来看,受到封禁行为侵害的企业应当首选《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内置的适用标准明晰与法律责任明确的条款作为主要的维权依据,而将《电子商务法》相关框架性条款作为辅助性维权依据。
总体而言,迄今没有一部可以统一与全面规制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违法行为的法律,公共权力机关与受侵害主体应当根据个案情形选择适用《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电子商务法》等法律追究实施违法行为企业的法律责任。
来源:人民法制网
图片新闻
-

河北井陉县:胡仁村作为试点村开了一个会
-

磁山——华夏第一粮仓
-

【国际锐评】中方对等制裁美方人员正当且必要
-

因限制使用特朗普推荐药物 美国卫生部门负责人突遭调职
热点新闻
- 天佑中华,山河无恙——中国(崂山)道家书画院刘玉平作品展 2020-04-29
- 孔庆旭-众志成城抗击全球疫情,中国艺术名家在行动 2020-04-28
- 央视侵权了吗?《明天,你好》原唱发微博维权却…… 2021-06-18
- 中国山水画王迎的艺术之路 2020-04-29

 京公网安备 11011502005563号-1
京公网安备 11011502005563号-1